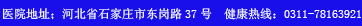读书人的敌人
2016-10-2 来源:不详 浏览次数:次作者:蒋蓝
摘自《极端动物笔记:动物美学卷》,东方出版社出版。
书蠹偶尔吃到诲淫诲盗之书,就会变成一种叫“无曹”的可怕动物,在身体内安家,人也就纵欲暴虐起来,女色、功名成为了行动指南;如果反其道行之,喂它过量的圣贤书也没有好结果,它吃多了就夜郎自大成为“玄灵”,住进人的大脑,控制思想的脉络。
——题记
书蠹是蠹虫庞大家族的一种,就是《尔雅》里说的覃(蟫,音银)鱼,即衣鱼,具有银子般的颜色。唐朝诗人寒山《诗三百三首》里就有“脱体似蟫虫,咬破他书帙”的句子,说的就是这种雅致但让爱书人讨厌的文字虫。书函成为蠹鱼的生活处所,就叫“蟫函”。蠹鱼的命名颇具匠心,因为赋予了虫子一种游动不居的滑行性质,就像它暧昧而精怪的字义。当然了,在文昌文祸俱生的时代,它还有一个杰出的名字就叫银鱼,听起来就很美。蠹虫在器物、书页里打洞穿凿,它们生存的痕迹为旁观者带来了意料不及的收获,出现了很多古怪的词汇——蠹怪(蠹虫的精怪)、蠹薮(蛀虫聚集的地方)、蠹贼、蠹蝎(水中的蠹虫)、木蠹等等,而蠹字(蠹虫所蚀书上字的痕迹)总是以诡谲的走向改变着汉字的内涵,就像一个异端侵入了大脑,在掏空记忆时,也留下了漂浮的手影。
古代热衷仙道的人,都预备一个木盒子,里面养书蠹,拿很多张写有“神仙”二字的宣纸喂养它,书法要尽量神骏、古拙,似乎字体能够传递元气。书虫如果三次都吃掉书中的“神仙”字样,虫就羽化为仙,称为“脉望”。脉望的故事出自《酉阳杂俎续集?支诺皋》,这成为古文人通过文字与天道沟通的精神证据。据文人们的描述,脉望像“肉的手镯”,但我估计其造型更像消瘦的饕餮,饕餮有狗的天性,总是喂不饱。或者说,脉望就是饕餮肚皮里的蛔虫。外国人缺乏中国人那种诗性的模糊印象,他们喜欢精细。赛尔伐斯特在他的《诗歌的律法》中,以不甚有风趣的词句,将它形容为“一种渺小的生物,蠕动于渊博的篇幅之间,当被人发现时,就僵硬得像是一团灰尘一般”。但是,西方最早对蠹虫进行研究的却是R.荷基,其在年由英国皇家协会资助出版的《显微画集》中,展示了作者对蠹虫仔细但有些荒谬的眼光。他说,这是“一种小小的白色闪银光的小虫或蛾类,我时常在书籍和纸张堆中发现,料想那些将书页和封面咬烂穿洞的必是它们。它的头部大而且钝,它的身体从头至尾逐渐缩小,愈缩愈小,样子几乎像一根胡萝卜……”“它头前有两只长角,向前挺直,逐渐向尖端缩小,全部是环节状,并且毛刺蓬松,颇像那种名为马尾的沼地芦苇……尾部末端也有三根尖尾,各种特征与生在头上的两只角相似,腿上有鳞也有毛。这种动物大概以书籍的纸张和封面为食物,在其中钻出许多小圆洞,也许从古纸在制造过程上必须再三加以洗涤锤炼的那些大麻和亚麻的纤维中获得一种有益的营养。”[1]尽管使用了工笔描摹的笔致,但读着读着,我突然觉得这银鱼变得好像不认识了,它被显微镜剥离了神光。
清人沈起凤在《谐铎?祭蠹文》里描绘说,蒋观察的藏书重地名叫万卷楼,半为蠹鱼损坏。他“命童子搜捕,尽杀乃止。是夜楼中万声齐哭,几于达旦,主人患之。”这种凄厉的哭叫乃是文字虫的生命之声。蒋观察不得不作一篇《祭蠹文》,以文攻文,于是才平息了蠹鱼们的叫嚷。
书蠹偶尔吃到诲淫诲盗之书,就会变成一种叫“无曹”的可怕动物,在身体内安家,人也就纵欲暴虐起来,女色、功名成为了行动指南;如果反其道行之,喂它过量的圣贤书也没有好结果,它吃多了就夜郎自大成为“玄灵”,住进人的大脑,控制思想的脉络。所谓控制思想,大概就是它的革命性转喻。
仅仅寄生在人身和器具中不过是书蠹的生存哲学,人们有很多方法驱除它。用以毒攻毒的办法,把鸡血滴进耳朵能杀死“无曹”和“玄灵”。但虫子可以转战南北,经常在肚皮里自言自语,却是令人惊怖的事情。有个文人叫吴曾,他写的《能改斋漫录》里,就有一条关于应声虫的记载,他是从陈正敏《遯斋闲览》转录的。
书载:杨勔中年得异疾,每发言应答,腹中有小声效之。数年间,其声浸大。有道士见而惊曰:“此应声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读《本草》,遇虫不应者,当取服之。”勔如言,读至雷丸,虫忽无声,乃顿饵数粒,遂愈。正敏其后至长汀,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环而观者甚众,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谢曰:“某贫无他技,所以求衣食于人者,唯藉此耳。”以上皆陈所记。予读唐张《朝野佥载》,云洛州有士人患应病,语即喉中应之,以问善医张文仲,张经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读之,皆应,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录取药合和为丸服之,应时而止。乃知古有是事。
现在的读者可以在《说郛》当中读到这则逸闻,好像这是在夸耀知识的通灵特性,但如果再读《本草纲目》,就发现事情正在发生尴尬的变化。李时珍是个诚实的读书人,他说,雷丸又叫雷实、雷矢、竹苓,药性苦、寒,有小毒辣。雷丸是真菌类多孔菌科植物雷丸菌的菌核,对于驱杀绦虫,疗效很好。现在说就是治疗蛔虫病和钩虫病。这样看来,所谓神乎其神的文字虫,从虚幻的灵台现身说法,不过是蛔虫而已。罢啦。
由美丽的银鱼演变为蠹虫以及蛔虫的过程,其实就是古代文字人蜕变的过程。这种钻营和穿凿的特征基本概括了文人在仕途上逶迤而诡谲的路径。因此,在佯狂炒作、卖名卖身之外,如何使文字虫如龙一般见首不见尾,一直是过于聪明的文字分子博取宫廷信任的最大心病。这让我联想起清人沈起凤在《谐铎?祭蠹文》里的观点:“借文字为护符,托词章为猎食,皆可谓书蠹。或曰,此等词义不连之辈,名曰书蠹,犹属过誉。”
技术就是思想。这是诗人欧阳江河说的,意境超迈,但我是从浅薄的层面理解含义的,技术更是锦衣玉食和美女如云。鲁迅先生曾经反复使用了“腹诽”一词,其实是从“腹议”化出来的,那么是否可以再分化出诸如“腹赞”、“腹颂”之类的词汇呢?不需要,因为赞扬从来就是高歌猛进的。应声虫在权力话语跟前没有缺席,它以一种复制和放大的功能发出了自己勤学苦练的声音。
作家郭正谊先生指出,中国一直有很多被称为“肚仙”、“灵鸽”的神人,自称有“仙人”藏在他们肚中,可以向“仙人”求问吉凶,去病消灾,十分灵验。招得大批善男信女,向其顶礼膜拜。其实“肚仙”讲话是“屏气诡为”,其声音发自“胸以上喉以下”,这就是其中的奥秘。
这必须提及腹语术。就是讲话向肚中咽声,使声音在腹腔共振,这样隔着肚皮就可以听到含混不清的话音。“腹语”练好了可以发出比较大的声音,不一定要耳朵贴着肚皮去听。有口技的人还可以练出不同声音的腹语。
学腹语不难,至少比拥有独立思想容易得多。只要倒吸气发音,或者强把话音往下咽就行。开始有些不习惯,慢慢就会掌握窍门,发音也逐渐清楚了。如果有兴趣,练上几个月,“肚仙”就练成了。
当“腹语”成为一门与口语、书面语并驾而驱的言说方式以后,它就摆脱了应声虫的尴尬处境,腹语可以更自如地表示当事人的赞叹。比如,在权力者一言不发干着一件事情时,腹语者就响亮地发出了一连串“好”的声音,这不是饱嗝声,而是一种类似饥饿的咕噜声,权力者明白得很,腹语人是饿了。因为从文字人在豪门高唱“莲花落”开始,必须回报,这是一种传统礼仪嘛。
腹语术经历了十几个世纪的演练已经炉火纯青。事实上,是古罗马人开始使用这个名称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腹语术成为了极受欢迎的娱乐项目,但也成为了文人们献媚的技术。腹语术就是读心术。要模仿的不止是他的表情,还有那些声音。而用腹语术来模仿逝者的语音语调,揣测别人的心理,这就是所谓的读心术。权力者的宏大叙事完全敞放出来之后,大众就会惊慌失措地露出马脚,这是破除异端的关键所在。说虽如此,但这多半是一种梦呓吧!
所以,在我二十多年的阅读写作生涯里,我从来小看“无曹”“玄灵”们的文字。如果承认“艺术最有力的武器是虚构,最危险的敌人是虚伪”是写作真言,我一直就处于“非虚构”的读状态,去亲近心目中的“非虚伪”写作。
本文说明:有关腹语术在日本的发展情况,文末参考了《神奇的腹语术》一文的结论,见由紀恵の部屋治白癜风专科医院头部白癜风怎么办